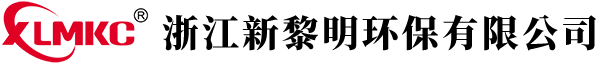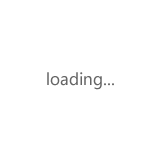车间外的马路门庭若市,都市的喧嚣被一道卷帘门离隔,只剩下东西磕碰的洪亮动静。
但萧立诚从不议论自己的故事,就像他从不答应任何一颗螺丝在他手里拧歪半分。
此时,他浑然不知,一道了解的目光行将穿越七年的韶光,落在他沾满油污的工作服上。

萧立诚却回身走向资料架,从一大堆零件中熟练地翻找出一个特定类型的尼龙衬套。
萧立诚关掉引擎,满足地用棉纱擦了擦手,在修理单上写下确诊成果和修理计划。
“立诚,又是你加班到深夜?这车王老板送来时说过,跑了好几家都没找出缺点。”

她是汽修厂对面“老唐家常菜”馆老板的独生女,大学刚结业,在邻近公司做文员。
他的班长,那个姓赵的老兵,拍着他的膀子说:“立诚,你小子天然生成便是干这行的料!”

老师傅老张从车底探出面,一脸尴尬:“老板,我这正拆着变速箱呢,一时半会走不开。”
“方位在机场高速连接线的应急车道上,一辆黑色奥迪A8,车牌尾号668。”
宋钦明凑近些,压低声响弥补道:“听车主的口气,来头不小,你处理得周到点。”

那种对东西的摆放次序,那种拆开和装置的节奏,那种查看每个过程时的纤细中止。
这绝不是一般汽修厂技师能有的方法,更像是一种通过饱经沧桑构成的肌肉回忆。